
By 吐露詩社 Tolopoem | 2021-08-16 | 文學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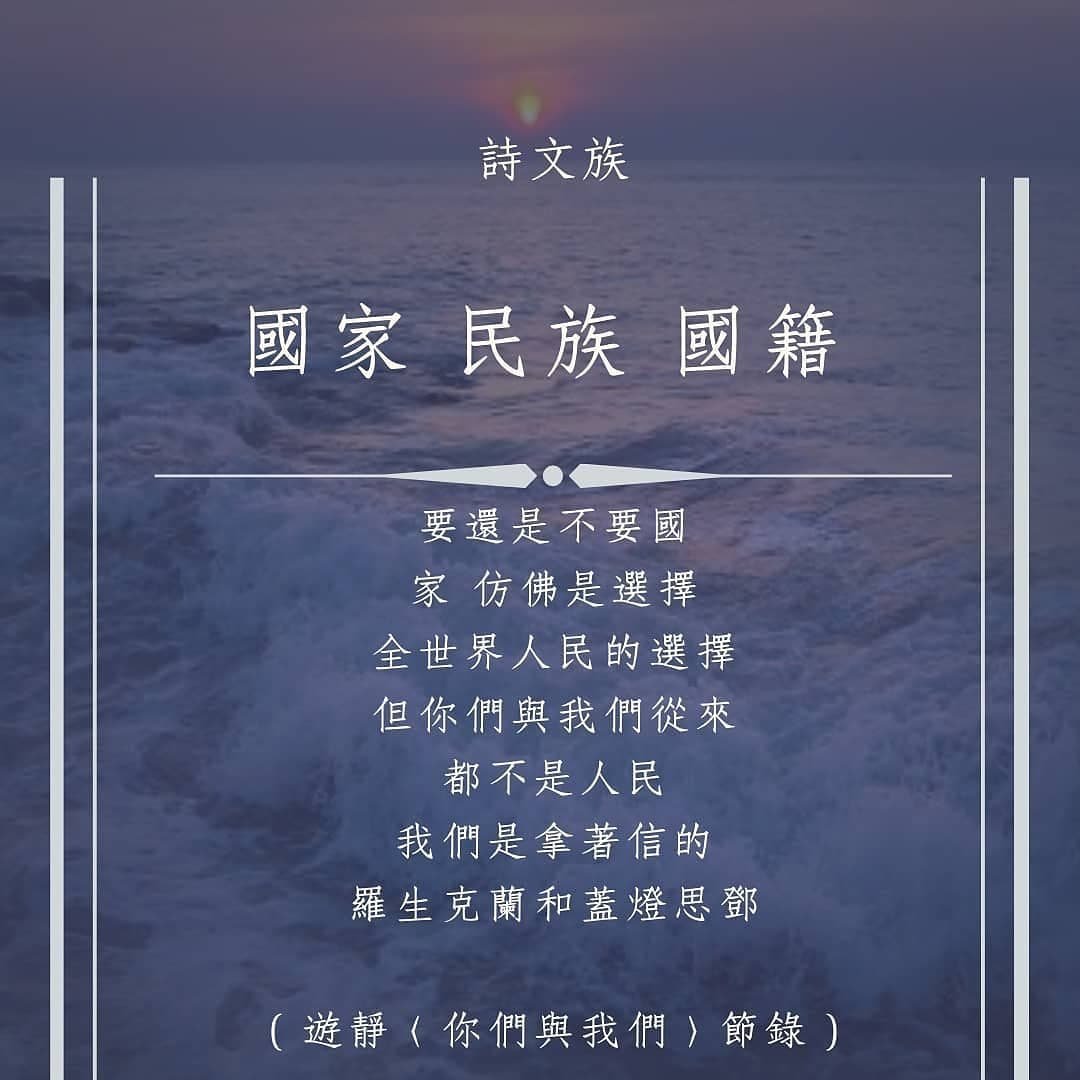
過去數回詩文族,每次只聚焦其一。這次,作為稍息的中途總結,我們走遠些,略談國籍、民族、國家的概念,思索虛構的民族,是如何透過詩、歌、文被逐漸構織,並隨之變異而流動。
國家/國籍/民族
國族不等於民族(nation)。民族的形成雖然與國家(state)有關,但nation一字更傾向理念與政治想象的意識形態,包含了尊崇公民的理想。進一步來說,由國族延伸的國族主義、官方民族主義其實是服務當權者的一種類型,用以支撐上層階級的國內地位,與「民族」所暗含的群體理想意志背道而馳。安德森把nation定義為「想像的政治共同體」,一種文化人造物(cultural artefacts),建構在人類深層意識之中,與歷史文化變遷相關,而非與生俱來、天然存在的概念。
「它是想像的,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,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,和他們相遇,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,然而,他們互相連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。」——亦即,我們透過想象力,與素未謀面的人建立了關聯性,由這種抽象的關係網絡所構成的,就是一個有邊界、有主權的、成員理應彼此平等關愛的共同體。
「政治愛」:
願為民族——人造物而犧牲? 為什麼我們會願意為一個有限的想像體而犧牲?民族的屬性猶如家庭、膚色、性別或出生的時代等,具有不容選擇、與生俱來的特性。在這種自然而來的連帶關係中,人類也許會體會到宿命感,一種「有機的共同體之美」(the beauty of gemeinschaft),從而,民族愛被理解為公正無私、不具有利害關係的,非常純粹的關係。為一個不是出於個人選擇的民族/國家(宿命)而犧牲,具有單純的道德崇高性。
詩/歌;語言/舌頭
「對於被壓迫者的語言的巨大隱私性的回應方式,不是撤退,就是進一步屠殺。」語言在漫長的歷史中浮現,跨越空洞的時間,使得我們每一個人與逝者產生聯繫。簡言之,印刷出版業促進了方言文字的了解與使用,進而藉由「讀者群」、「書寫者」的身份構建了最初的民族共同體概念:有一群(抽象的)人正與我閱讀同一個語言,儘管我們互不相識,但依然擁有相同的信念、理想。
方言(dialects):
語言學上,方言指的是同一個語言的變種(variants),若兩種語言的演化到不能理解彼此時,已經屬於獨立的語言。而中國的所謂方言定義,包括閩南語、粵語,都是兩種獨立的語言(language),國語/普通話/之所以成為標準語,完全是出於政治的考量——假定使用同一種語言,某程度上可以增加民族主義的熱情。
侯孝賢電影《悲情城市》,講述1945年台灣脫離日治,恢復國民政府統治後發生的二二八事件。後天受傷聾啞的角色林文清,象徵了日語世代的台灣人被剝奪語言,並因國民黨打壓而失去說話的權力,乃至二二八事件的不可言說,台灣人在台語、普通話、日語(外省人/內省人/日本/台灣/中國)之間流離,造成身份及文化認同上的割裂,墜入失語無聲的絕境。
什麼是無國籍?
現代社會中,民族歸屬是一個基本、普遍的概念,如血緣、年齡、宗教。一般的理解是,所有人都與生俱來地擁有一個民族的身份。然而,事實上有一群人不被任何國家承認身份,不屬於任何一國,在國與國的邊境夾縫之間生活。
日本國內的「無國籍」:
2020年底,日本的無國籍登錄人數仍有1397人,未登錄的不計其數。
台籍華僑:陳天璽是在日出生、成長的華裔,雙親是留日的台灣「外省人」。1972年,中華民國、中華人民共和國、日本三地外交關係改變,她喪失中華民國國籍,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無國籍漂泊時期。自幼她深信祖籍歸於中華民國,卻因未曾長居台灣而不被承認戶籍,入境祖國時需辦理簽證。另一方面,她在日本土生土長,有永居權卻無國籍身份,回到成長之地,也要提交入國許可證明。
陳天璽提出的疑問是,無國籍本身,能成為一種民族的認同感嗎?同時,擁有國籍,卻對自己國家愛恨交加的人,也是另一種形式的「無國籍」嗎?
最後,引《想像的共同體》關於「齊唱(a capella chorus)」的部分作結:
「如果我們知道,正當我們在唱這些歌的時候,有其他的人也在唱同樣的歌——我們不知道這些人是誰,也不知道他們身在何處,然而就在我們聽不見的地方,他們正在歌唱。將我們全體連結起來的,唯有想像的聲音。」
引用自:
陳天璽著、馮秋玉譯:《無國籍——我,和那些被國家遺忘的人們》,新北市: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2016年。
班納迪克·安德森著、吳叡人譯:《想像的共同體》,臺北: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2021年。
編者:zita
本文經授權轉載自<吐露詩社 Tolopoem>專頁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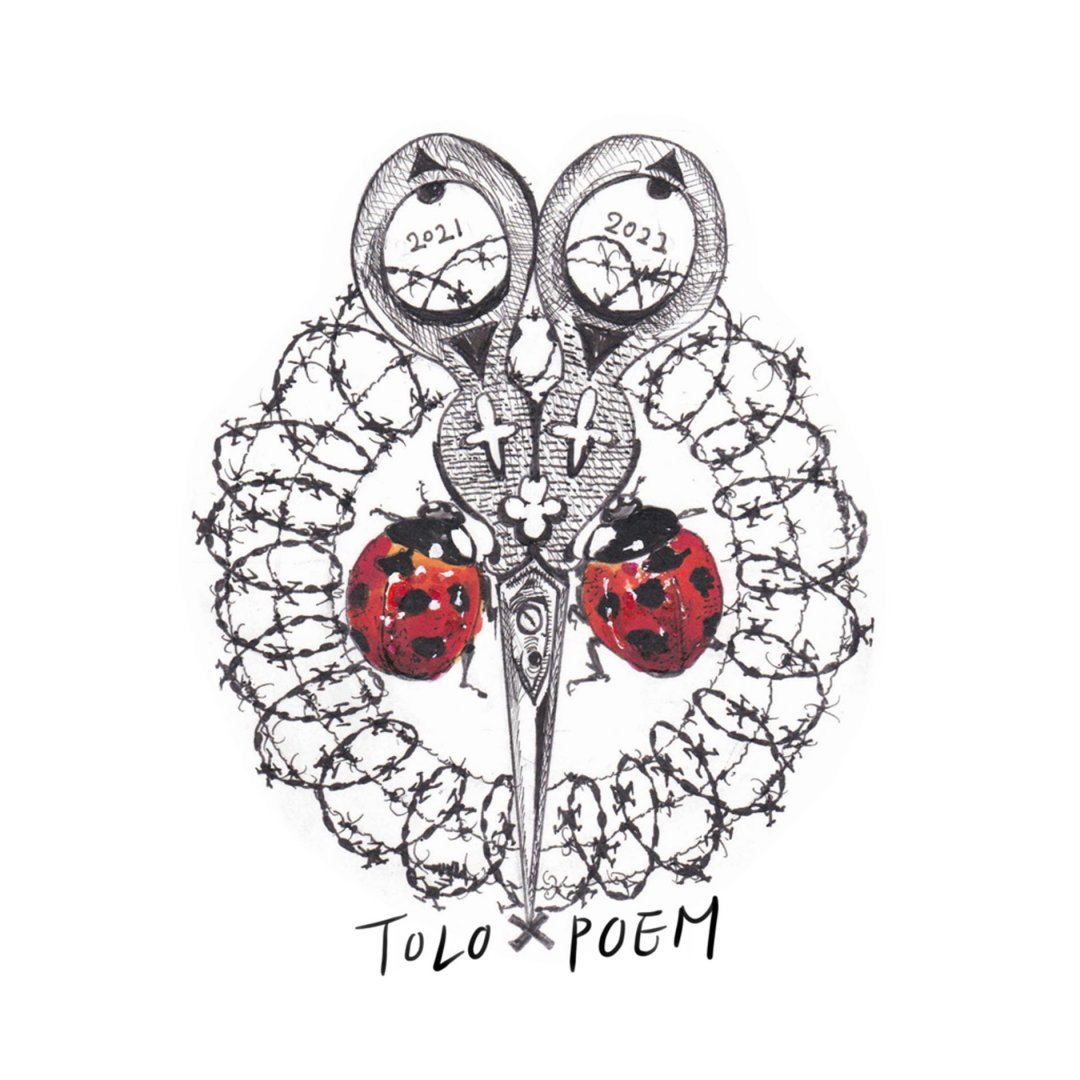
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2021-2022年度吐露詩社
文學藝術
詩蝨晨騷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〈晨〉
鐵絲網灰的清晨
國境邊陲漫長如環形路軌
一群蝨似的人讀詩,眼睛
就越過水泥紅磚牆那崩塌洞口
看一顆圓形雞蛋大小的天空